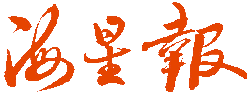
朗读

枇杷果儿
●周雪松/文
其实,我从未吃过枇杷果,也不知道枇杷树长什么样。不过,我年幼时便对这名字十分好奇,因为它并非是我所知悉的常见俗名,比如桃儿,杏儿,梨儿……枇杷,这名字乍听来,似乎从志怪小说中来,那么它自然不该生在寻常之处,是生长在高耸入云的青城仙山,还是瘴气缭绕的蛮荒之地呢?那时,我在北国,没有机会见到枇杷。后来,我到江苏徐州读书,见到诸多异于故乡的风物,我说的并非是花市里争奇斗艳的盆栽,而是真正生长并根植于某一片土地,沐浴某一寸阳光,呼吸某一口空气的植物。
可是,我还是没有机会见到枇杷树,而且,还曾闹出过笑话。有一次,我应朋友之约,到中国矿业大学老校区去游玩,见到了山上小径旁长了数株灌木,长长的枝条,开着紫色的小花,有些树皮已脱落,树干光滑,朋友见了称奇,问我此为何物?我其实并不知道,脑海里却瞬间闪过了“枇杷”之名,随口应答,“是枇杷吧”结果几个人凑到近前,那旁边立了木牌,“紫薇”是也。朋友随即大笑,不知道便不知道吧,看也不看,还说什么枇杷,我满脸通红。
后来我才知道,历史上也有一宗关于枇杷的争论,宋代的大学士苏东坡有首诗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”有人问,卢橘是什么果子?东坡居士说,枇杷是也。后人多有辩驳,比如李时珍就说:“注《文选》者,以枇杷为卢橘,误矣。”当然,卢橘是枇杷的说法依然延续到近代,相比较而言,苏学士所说似有几分道理,而我所说的紫薇是琵琶实属胡言一派了。
究竟枇杷果儿为何物呢?
我的书桌上就放了数枚,蜡丸大小,有绒毛,半青不黄的,放到鼻子近处闻,有淡淡香气,剥开食之,酸大于甜。听说枇杷果与樱桃和梅子并称“果中三友”想说,樱桃红,为俏丽,梅子青,为俊朗,枇杷黄,为哪般姿色,我一时想不出。直到翻阅资料的时候发现,历代中国文人画,有很多以枇杷为题材,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枇杷孔雀图》(宋·崔白)和《枇杷猿戏图》(宋·易元吉)都是艺术珍品,而近代的国画大师任伯年、吴昌硕等人也常常将枇杷入画,与宋人的高古之意不同,今人们似乎有意的接地气,总之《枇杷孔雀》也好,《枇杷凤仙》也罢,事实证明原来这朴实的枇杷果儿,一直与光阴和生活同在。
我端详着书桌上的数枚枇杷果儿,似乎想得到它生于何处长于何处了,它不仅可以生长在深山密林,更难能可贵的是,它们能够生长在农家的庭院之中,我似乎看见了顽皮的男童上树摘枇杷果儿,然后跳下来相互追逐嬉闹的场景,也似乎看到了有一位慈祥的阿婆手里捧着枇杷果儿,蹒跚走来……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