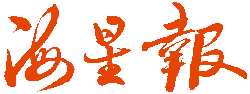
朗读

写信
● 周雪松
近日,在北京当兵的堂弟来电,我们相谈甚欢。突然觉得那个全家人公认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也长大了。我说,“你打电话不方便,可以写信给我。”“写信?我从没有写过信,我上学那会儿写情书都不流行了,谁还写信呢。”他说。
好吧,我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某些记忆正逐渐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中,如同那些尘封在我们抽屉最底层的书信一样,纸张由白变黄,文字也由深变浅,而许多故事也终将在某一个孤寂的月夜里沉沦。
我自幼在祖父母身边长大,除了被疼爱呵护外,还耳濡目染了老一辈们诸多老习惯,比如写信。我的祖父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,读了师专以后,就当了小学的教员。我的祖母是旧社会大户人家的女儿,满族人,也读了两年书,可是嫁给我祖父时家道已经中落。他们辛辛苦苦的养育了五个儿女,经历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十年浩劫。好在我出生的时候一切都已风平浪静,祖父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中国乡村通讯尚不发达,距离稍远的亲朋好友间的联系还多半是靠写信,我也是在那时初识得书信的况味。我的祖父常写信给我的舅爷(我祖母的胞弟),他们一个在东北、一个在湖南,相隔数千里,唯有书信遥寄相思。乡下人家是没有信箱的,所有的信件都是邮递员直接送到村委会,然后村委会的广播员用大喇叭广播:某某某有信,某某某有包裹。我记得祖父常常端坐在椅子上,读信给祖母听,而祖母也时常感慨在外乡漂泊了几十年的弟弟。
偶尔,我也见到有邻居找祖父代笔写信,祖父从不拒绝,于是那人坐在书桌旁口述,我祖父写,那人说完了,信也写好了,然后再读来听听,问问哪里不妥当,还有什么要补充,这听起来是旧电影里的情节,但事实确乎如此。
我常常觉得写信是一种才华,可惜等到我能写信的时候,电话已走进了千家万户,除了年长的人,谁还有会花心思和时间写信呢。因为电话里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,即简单又方便。闲时就整理整理以往的书信,有时也一次次的翻开读一读,似乎又可见到彼此斑驳的光影,有年少轻狂,豪言壮语,有感慨世事,略晓浮沉,更多的是生活琐事,彼此关心……
我对书信的感情是什么呢?是对往日的无限眷恋还是对今时的不满?是想见亲人而不能见的因由,还是因为过于忙碌而忽略了的那颗旧心?都有吧。
纵使有电话,有短信,有视频,有微信,我们可以不见面的呼喊,但我们却遗忘了彼此写在光阴里的声音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