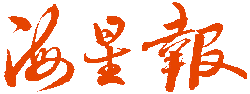
朗读

尔来几个秋
● 文/周雪松
不知不觉已过了立秋时节,天气终于渐渐凉爽下来,只一阵微风,叶子就扑簌簌的落下,也不知有多少秋虫在萧萧的雨中殒命,遂想起秋收时乡下农田里的蚱蜢,呆呆地伏在渐枯的玉米秆上,再没有嫩叶可啃食了,再没有露水可豪饮了,此时清冷的露水还能如往常般甘甜受用麽?总之,虫儿们没再有跳跃的气力,也不再敏感于任何声响,哪怕人们的脚步逼近,这气息未免然人难过而心生悲凉。纵使万物由盛及衰是自然之造化,且自幼稚园始我们就知道“春夏秋冬,四季更迭”的道理,面对此景,情何由来?
借景抒情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们的情怀,也不必查阅先人的诗词章句了,如此景致,恐怕也只有“人比黄花瘦”般离情罢了。当然,确乎有人陶醉于秋生之处,这是极少有的。除了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刘禹锡,王居士(摩诘)算是佛心了得,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于诗画之间给悲观论调者以极大的信心,还有主席诗词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给很多年轻的不羁的心予勇气和理由,但是,真正能够山居享受秋暝的有几人?真正有此豪迈气概的又有几人?此境界与胸襟可遇而不可求。
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”人们常常看花而少于世界,看叶而忘于菩提,法国作家蒙田说:“生之本质在于死”十几年前读到,至今才有所体会,生与死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存在状态,可恰恰是有生必有死,有死方能生,由此观之,此秋何悲?彼秋何喜?年少时学习书法,有师云:“要在乎字里,更在乎行间”,日后对鉴赏略有心得,所谓字里行间既要体现单个字的功力,更要体现字与字之间的联系。关键在于变化:浓淡、轻重、缓急,在变化中取意成象,此妙趣也。
万象如是,在生命的长河中若确乎有终极存在,莫不若你我与环境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和关怀,与时偕行也好,时行时止也罢,终究归于我们对于“时”的把握,不患一时之得,不患一时之失,古往今来,“彼”与“此”二字,互为体用,未见分离。
正是:“秋风知我在,何苦等三年,无心少年月,有意不再欢,依依与杨柳,尔来几个秋,默默不作答,只有叶叶飞”。












